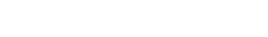老穆终于还是搬到了儿子家。
他小心翼翼地掀开书桌上的玻璃板,把平平整整压了十几年的照片一张张抽出来,认真地夹回相册里。
相册的封面上是十年前老伴去世的那个下午,院子里的山楂树被阳光镀成金色,小豆子踩着那把他退休时从工厂里带回来的老板凳,仰着小脑袋,就差一点点便可以够到那颗丰满的山楂了。
山楂树还在,只是临近初冬,叶子枯啦啦掉了一地。
老伴走后,山楂依旧年复一年结得丰盛,收下来送些给左邻右舍,剩下的也够他过个年了。
但今年不一样,他知道挨不到过年这片老房子就要被拆了,自己早晚会走,索性把收下来的山楂送个精光。老穆串一家门,就不由自主地拉起几十年前这片胡同里的家常事儿。
自从老伴去世后,这片胡同越来越多的老人相继离开。有的被儿女们接走,有的住进了医院,有的安静地睡了过去,再也没醒。
前些日子,跟老穆从小一起光着屁股长大,后来又一起在修理厂工作了一辈子的老钱患了痴呆,老穆便天天抱着自己的宝贝相机和影集去给老钱讲故事。老钱坐在老穆对面,傻呵呵地笑,老穆捧着老红梅,“咔吧”一声就把老钱拍下来。
老穆翻到老钱刚进修理厂那会,不自觉地笑了出来。
老钱浓眉大眼,年轻的时候那叫一个俊气,每次骑着上海“永久”叮铃铃穿过巷子,总会惹得情窦初开的女孩子们躲在门后偷看。
老穆跟老钱是死党,也经常借老钱的永久骑过一条又一条巷子,耍个酷,潇洒一回,但女孩儿们总是不留情面地识破他,捂着嘴冲他得劲儿笑。
那个年代,好像每个人都有一件珍贵的宝贝。
上海永久是老钱的宝贝。常州红梅是老穆的宝贝。每个傍晚,当老钱停下自行车,蹲在巷子口用干净的棉布对着永久仔细擦拭的时候,老穆正哈着气一遍又一遍抚摸着自己的红梅。暗恋老钱的女孩子都会在梦里坐上老钱的车子,吹着微风,晒着阳光,抱着老钱的腰穿过大街小巷。暗恋老穆的女孩子都会在梦里成为他红梅中的主角。
这阵子天气不大好,雨水不断,又湿又冷,老穆的风湿又犯了。多年的老毛病,他倒是不在意,让他心情不好的事儿不是这个。
老穆发觉自己变得越来越奇怪。他开始害怕儿子的奥迪车出现在巷子口,害怕陌生人出现在巷子里,害怕翻开那本珍藏多年的影集。
每个周末,老穆都会大清早起床,把屋子上上下下收拾得干干静静,然后从阳台上搬回两盆薄荷草放在棕色的木茶几上,锁上门,出了巷子左拐,便到了张小根理发馆。
老张这人爱睡懒觉,老穆又不去叫他,总是在镜子前的大圈椅上坐很久,才会等到老张慢吞吞地从里屋出来。
老张的理发馆几十年来很少关门,哪怕过夜。除非风暴天气,歪歪扭扭的木门被折腾得喘不过气儿,他才会在屋子里勉强拖过大圈椅靠在门上。
坐在老圈椅上对着镜子,老穆总喜欢掐着指头算。算算老张的理发馆,一开就是三十多年啊。
老张并不是本地人,从河南北边入赘过来的,也就几百公里远。老伴走后,他也没想过回去老家看看,听说老家已经没人了。
老张是胡同里唯一一个无儿无女的老人,曾经有过,但不大的时候丢了,没能找回来。老伴因为这件事受了刺激,疯疯癫癫地过了大半辈子,终于糊里糊涂地走了。剩下老张独自看着店子,倒是自在,想睡便睡想吃便吃。逢年过节,也大开着门,不用麻烦走亲访友。
老张也有宝贝。那个跟了他三十多年的推子一直不肯换,牙齿都快磨光了,但像老穆这样的老常客还是习惯让它在脑门上走,心里舒坦。电推子老张倒是有,却不常用,偶尔拿出来推推小毛孩。
再年轻些,胡同里的月亮再俊朗些的时候,这铺儿倒很热闹。尤其元宵,街铺子门前挂满彩灯笼,彻夜不息。花鼓队敲锣打鼓走街窜巷,每过一个十字路口便要停下来吹打一番。小孩子挑着花样繁多的小灯笼,一个劲儿地跟着热闹跑,大人们追都追不上。那老戏堂子里还演着眉户(编者注:陕西省的主要戏曲剧种之一),三弦声声,曲调婉转,又是《梁秋燕》。老话说得好:“看了梁秋燕,三天不吃饭”,老穆可整整看了大半辈子,依然觉得新鲜有味儿。
老张的理发馆就开在戏堂子对面。平日里,不分白天黑夜,戏堂子总聚着些吹拉弹唱的闲人,顶多五六点太阳压山那会推着自行车到附近的幼儿园接趟娃儿,都来不及送回家,又迫不及待地折回堂子里。
来老张理发馆的客人总喜欢翘着二郎腿跟着堂子里传来的曲子哼。老张对戏并无知觉,糊里糊涂听了几十年却只记得刘二嫂那句:白羊肚手帕花牡丹,黑油油头发双辫辫,绿裤子粉红衫,桃红袜子实在鲜。
说起这些,仿佛都是前些儿刚刚发生的事。现在戏堂子静下来了,老张竟有些不习惯,晚上睡觉都不很踏实,就连那些很依日子的老常客也少了很多。
老穆披上白围布,坐在镜子前开始发呆。围布灰得不像样子,还有股异味,大概是很久没洗了。
老张真是懒得不像话,昨天掉的碎发末只扫成了堆儿,也不撮掉,白花花的又散了一地。
老穆不自觉地打了个盹,清醒后扭头朝里屋看了一眼,还得过会儿老张才能起来,便又拿过倚在墙角的笤帚,犄角旮旯扫了一回。
街上人渐渐多了,越来越多的车子进来,喇叭催着,吵醒了老张。老张又是那句骂话儿:娘个鳖孙,地篓子可空着多,急个逑!
老张只管给别人理发,自己的头发却懒得打理,胡茬子经常忘了刮,显得整个人没精神。脚上的塑料拖鞋底子也快磨透。一年四季都套着的那双深蓝色的尼龙袜子,趾头尖的破洞终于被生拉硬扯地缝上了。
对话不多,也就是些胡同里再平常不过的事,溜过推子的齿缝,伴随老穆的碎发,不紧不慢地往下掉,或飘上一阵。
“该进城了,咳咳,染些黑吧,咳咳,儿女们见了也喜欢。”老张嗓子堵着痰,话儿间总咳个不停。
老穆望着镜子呆了几秒,“嗯……染个吧,染个吧,小豆子下午就过来了,这白的吓着他。”
“小豆子高中了吧?”老张问。
“嗯……高三了,高三了,过年儿就该高考了。”老穆一说起小豆子就不呆了。
“唉,这日子急的,你看看……催着埋人咯。前眼我还听得见对堂子里的戏呢。”
“该走的都利利索索地走啦,老骨头一把的也拖累人,可别像老钱那样,活得断味了。”
“明天该去给老钱打扮打扮,这指不定哪会儿就过去了,见都见不着。”
街上的阳光渐渐淌进屋子里,他们半个身子被淹了进去。有闲人来窜门了,拉个小板凳,坐下就开始漫话儿。老穆时不时插上一句。老张也说,但并不停下手里的活。
隔壁王太过来,恰是老穆刮完胡子的时候。他们总是碰在这个点上,日子一多,倒觉得有意思了。像他们一样,这铺子里的老人们大都用不着看时间,他们凭着习惯生活,凭习惯活着。
从张小根理发馆出来,经过一家杂货铺和一家寿衣店,便到了老市场。
老市场由一条石板大马路隔成两半。左边是锅碗瓢盆等等各类生活用品的门面,门前密密麻麻摆满了杂货,只留一条小路可以走进店子。右边有小饭馆、澡堂子、旅馆、发廊杂乱排列,尽头是一家托儿所。都是些七八十年代的房子,相比胡同而言,算是新的了,但看起来破破烂烂年久失修的样子,不过很快就要连同胡同一块拆了。要不了几年,这里将与市区接壤,成为一片新的城区——一个会让这里的老人们迷路、找不到家的新区。
沿着青石大马路走,尽头就是菜市场了。新鲜的蔬果绿的绿、红的红、紫的紫,样样有样样的颜色,油亮亮的招人眼。狗儿们抽着鼻子人脚下乱撞。
老穆习惯在刘寡妇摊上买番茄和芹菜。刘寡妇才刚三十岁出头,一个人拉扯着一儿一女真不容易。老穆又转去王老头摊上买土豆。王老头的土豆又小又多疤,而且味道不怎么好,但他倍受儿女冷落,怪可怜的。之后老穆才去阿发家。
阿发家是个两百多平米的大铺子,卖水产、猪羊牛肉以及手工馒头。小豆子喜欢吃阿发家的馒头和卤肉,但老穆总会顺便买一条鲈鱼回去。阿发家的鲈鱼顶好。
清蒸鲈鱼是老穆的拿手好菜,也是老伴在世时最喜欢的一道菜。每次看到鲈鱼,老穆都会想起老伴吃鱼时候的样子。她夹着一小块嫩白的鱼肉慢吞吞地送进嘴里,挤着干瘪的嘴唇抿啊抿,细细的白刺儿便听话地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。大多时候,老穆都会把挑好的不带刺的鱼肉夹到老伴碗里,不过老伴还是那样挤着嘴抿啊抿,好像这刺儿永远都吐不完似的。
老伴是土生土长的南方人,二十岁从长江下游嫁到黄河中游,几十年来也适应不了北方的习性。每当一场又一场的风暴卷着黄沙横扫关中大地,她就像一头受惊的老虎,充满恐惧与躁怒,独自穿梭在茫茫瀚海中,试图向南,忘了身后所牵连的一切。
时间愈久,她越是不能自拔,以至于后来每次吹起沙尘暴,她的脑袋里便似有棒槌击鼓,浑身跟着鼓皮震颤。这个时刻,她发疯似的想逃跑,想回到家乡的河岸,老老实实地跟着父亲贩卖水产,再乖乖地嫁给孙二虎,随他跑一辈子货船。
老穆偶尔也会在风暴天儿里顺道想起孙二虎,再撩起袖子摸一摸自己小臂上的伤疤。那是孙二虎用烧红的钳子烙下的。
那时候老穆借住在孙家那间破旧的杂货屋里,孙二虎的屋子就在他对面。孙二虎每天得眼睁睁瞅着兰子在对面的破屋里进进出出,独自苦恼。
孙二虎才是跟兰子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人啊!他带兰子抓鱼,教会兰子爬树和游泳,还跟兰子在野兽出没的深山林子里一起迷路共度漫漫长夜。凭什么这个北方汉子一来,一切都变了。
兰子疯狂地迷恋这个遥远的北方来的小伙子。她全然不顾老爹和孙家十几年前便订下的那门娃娃亲,也把与孙二虎一起长大的那段欢乐时光弃得一干二净。跟孙二虎比起来,穆小伙才是那个不仅能让兰子欢乐,还能让兰子忧伤苦恼的人。
于是,在一个大冬天里清冷的早晨,孙二虎抽出火炉上烧的通红的铁钳,一脚踹开穆小伙的屋门。穆小伙起个大早,正摆弄自己的宝贝红梅。孙二虎一钳子烙在穆小伙的胳膊上。穆小伙疼得龇牙咧嘴,摔了红梅,恼怒地跟孙二虎干起来。
毕竟是背井离乡寄人篱下,这一冲动,老穆不得不离开了,可他还没有拍到心目中最完美的长江落日,但兰子鼓足勇气的一个决定,完美地弥补了他的遗憾。
他们在一个美得不像话的落日里,奔向北方。兰子知道,这一步迈出去,就再也别想回头。
跟老穆有了两个孩子之后,兰子曾写过好几封信回去,终究没有回音。她也再也没有精力和勇气去寻回家乡了。虽然北方的一切都令她难以忍受,但只要老穆在,她就离不开他。
沙尘暴里的兰子让老穆害怕,让老穆愧疚,但他只要一想起兰子临走前那个满足的微笑,又会欣慰不少,所有的不安和愧疚也都被现实所冲淡了。
并不只有老穆才有这样冲动而又无悔的岁月。阿发也正经历着滚烫的青春。
在亲朋好友眼里,阿发可不算个好小子。他十八岁,跟小豆子一样的年纪,却已是社会上闯荡三四年的小混混了。
阿发初中就开始跟着一帮不爱学习的人抽烟打架谈恋爱。在一次集市上,阿发玩飞刀,扎死了胡老头心爱的驴子。胡老头是出了名的难缠,先是把这件事闹到阿发家和学校,后来又闹到派出所。结果是阿发被学校开除,阿发爹赔给胡老头五千块,把死驴子拉回家。所以那段时间阿发家的铺子里多了一种驴肉。
老穆从来不买驴肉的,但阿发爹砍了一大块硬是塞进老穆的菜篮子里。阿发爹说:“又到星期天啦,小豆子该回来了,小豆子真有出息,聪明会念书,这肉给小豆子吃的,好好补补他,吃好了身体才能念好书嘛!”老穆于是也就不推辞了。
阿发还去内蒙混过一段日子,回来后身边多了一个女孩,看起来要比阿发小个两三岁的年纪。铺子里人人见面就不再说鹿酒鬼打他老婆的事了,而开始谈论阿发跟那个女孩。有人夸阿发长本事了,不掏钱的媳妇都能领回来。有人感叹阿发这孩子太混,阿发爹真够倒霉的。
阿发经常给胡同里各家送东西,每次来到老穆家,都会问些关于小豆子的事。他跟小豆子从小玩到大,有感情。但小豆子去城里上学后,他们就很少见面了。即便每个周末小豆子都会被带回来过上一天,但小豆子他妈不允许小豆子再找阿发玩。
本内容来自每天读点故事www.dudiangushi.com,为作者原创作品,请尊重版权,侵权必究
老穆很喜欢阿发。在他眼里,阿发是个懂事又敢干的小伙子,颇有他当年的风范。只要一跟阿发说起小豆子,老穆便滔滔不绝,末了还嘱咐阿发多跟小豆子联系,给小豆子讲讲阿发自己的事。
从菜市场回来,经过老钱家,老穆便会推开门进去,为老钱放下一提豆腐干,并嘱咐照顾老钱的保姆把豆腐干切成丁,放点葱花和陈醋凉拌。这可是老钱最喜欢吃的菜。再跟老钱说上几句话,老穆就走。老钱的猫总是在这个时候溜出门,紧紧地跟上老穆的脚步。老穆任它跟,不驱它回家,它会慵懒地躺在老穆家的花台上呆个半日,差不多夕阳落尽的时候,自会慢悠悠地回去。
老穆养过一只苏格兰折耳猫,经常被老伴抱着在山楂树下的躺椅上晃悠晃悠。老伴走后,猫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,哪里都找不到。
后来隔壁王阿婆的土猫生了一窝灰白灰白的猫崽,可爱得很,老穆专门跑过去看,最终也没能下决心抱养一只。
老穆搬了一把小椅到花台边,择菜、杀鱼。将近中午了,深秋的阳光干净明亮,没有一丝焦躁的热,暖洋洋地洒了一地。山楂叶子偶尔飘落一两片,静静地躺到地上。邻家的院子里间或大人说话小孩吵闹的声音,夹杂着几声狗吠。
小豆子终于来了。老穆和一桌子菜已经在客厅里等着他了。跟小豆子一起来的还有儿子儿媳以及女儿一家。一大家子人都齐了。算是给老爷子搬家吧。
门一被推开,便是嬉笑吵闹的声音,家里好久没这么热闹了。老穆突然觉得有点慌,就连躺在花台上猫也受到惊吓,蹿回屋子里,又蹿出去。
女儿开始了一贯的唠叨:“爸,我不是跟你说了嘛,衣服床单换下来先放着,我来了给你洗!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发霉啦,该扔的就扔!你闻闻这屋子里味儿!还有,南屋又不住人,都放些杂货,你收拾那么干净干嘛!
女儿在屋子里一阵翻腾,她打开箱子盖,“唉爸呀,你这些东西还攒着呐!你说说你攒这些玩意儿干嘛,都多少年了,还留着我们穿裤裆的玩具!还有小豆子的东西。来来来,豆子来看看,哈哈,这不是你小时候最喜欢戴的猴脸面具嘛,为了争这破脸,还跟你妹妹打了一架!记不记得?哎呀,你这小子小时候可真不是个好惹的主儿,什么好东西都被你占了!一点都不知道让着你妹妹……”
从一进门老穆就发现小豆子脸色不对。他并不像以往那么爱说爱笑了,不管谁跟他讲话,都是垂着眼睛始终不看人。老穆看着他一脸苦大仇深的样子,忍不住笑起来:“谁惹我们家豆子!我罚他站门槛!站烂为止!”
在儿子小时候,孙子小时候,老穆都是拿这句话吓唬他们。现在他们都长大了,老穆还是喜欢这么说。可豆子翻了个白眼,根本不理,自顾自低头玩手机。
儿媳看到豆子那副表情,皱了个眉头,一把夺下他手里的手机,开始不厌其烦地说教:“爷爷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啊!以后手机也别想拿了!”儿媳又转过头来看老穆:“爸,你说说这孩子还怎么管!气死我了!皮得不像话!马上就要高考了,还是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!这也算了!可你不知道,他竟然在学校谈恋爱!要不是他班主任告诉我,我和他爸还被蒙在鼓里呢!我就说怎么每天晚上回来那么晚!还骗我说是学校加了一节晚自习!没想到是天天晚上送人家女孩子回家!”
……
终于开饭了,儿媳妇的嘴巴却还是停不下来:“从下周开始,晚上下课你爸去接!中午必须回家吃饭!你爷爷今天就搬过去跟我们住了,以后周末也不用上这儿来了。我给你报了补习班,一天三百多,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去上课!明年要是考不上,你自己看着办!我也不管你了!”
儿媳的语速快得任何人插不上话。老穆有些烦躁,敲了敲碗,“吃饭吃饭!有什么回头说!豆子好不容易过来歇歇,还这么看着他!”
“爸!你看看,这都是给你惯的!”儿媳的嘴无休止地响,终于被儿子一声喝住。
这顿饭就这样因为儿媳变得苦涩无味。老穆看得出来,小豆子一个字都听不进去,这些话对他没有丝毫作用,反而会触怒他。他在强忍着内心的狂躁和叛逆,表情显得有些扭曲。要不是儿子和女儿在中间调和几句,小豆子怕是要哭出来了。
儿媳对小豆子的专断让老穆极看不惯。可他却无能无力,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跟小豆子逗趣了。
终于。
终于开始收拾了。小豆子一言不发,面无表情地搬东西。
老穆割舍不下的物品太多。他扫荡式地把那些东西一件接一件摆进收纳箱,满了,又掂量着找出一些不那么重要再拿出来,摆回原位。他知道,这一走,回来就变得遥不可及了。
山楂叶子在频繁地掉落。邻家的狗吠、说话声、孩子的吵闹此起彼伏,却显得格外宁静。老穆站在院子中央,看了一遍又一遍。每个角落,每一处花草和声音,屋顶的每一片瓦片,都恨不得跟老穆走。老穆锁上门,钻进儿子的车里。
原来他带走的东西并不多,只是三个不大的收纳箱,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车子的后备箱里。儿媳终于不再说话。小豆子插着耳机耷拉着脸。儿子专心地开车。
车子安静地驶出胡同,拐到铺子街上。老穆按下车窗,有股凉飕飕的风吹进来。车子经过张小根理发馆,慢下来。老穆伸出胳膊跟老张打招呼。老张正在给人剃头,老张和剃头人一块儿转过脸冲着老穆笑。
老张扬着手里的推子喊:“走了哟!”
老穆回:“走了…走了……”
连同那些古旧的岁月,一起走了。
冬将至,空气干冷,老穆还是习惯穿老伴买给他的那件厚棉衣。吃过晚饭后,老穆乘坐电梯,从二十楼下来,穿过小区里一栋又一栋楼房,穿过灯火阑珊的街口。
广场上早就开始热闹起来。老穆绕着广场走了一大圈。
老穆穿过玩轮滑的孩子,穿过练习街舞的少年,穿过踢毽子的中年人,终于找到昨天来过的地方。他有点累,坐到喷泉边的长石阶上。喷泉并没开,时不时地会有年轻的小情侣们手牵手从喷泉上走过,看起来跟小豆子差不多的年纪。
眼前是节奏轰鸣的老年舞蹈,在彩光流溢的广场中,像一片初升的朝阳。但老穆,并不喜欢。可他又没别的地方可去。
编者注:本文为#味道#主题征文作品。